當京東“國民好車”埃安UT super的最終成交價定格在屏幕上時,這場吸引了近30萬人圍觀的拍賣活動被推向了氣氛的最高潮。
對于參與其中的廣汽而言,與其說這是一次新車首秀,不如說更像一場精心策劃的品牌營銷。先是京東官宣“造車”,后又是京東進一步解密,曝出了和廣汽“聯合造車”的經營思路……
這一系列合謀雖然不代表埃安實現了品牌向上,或許甚至也不能給這款新車提升多少銷量,但它給了目前最需要的東西——流量和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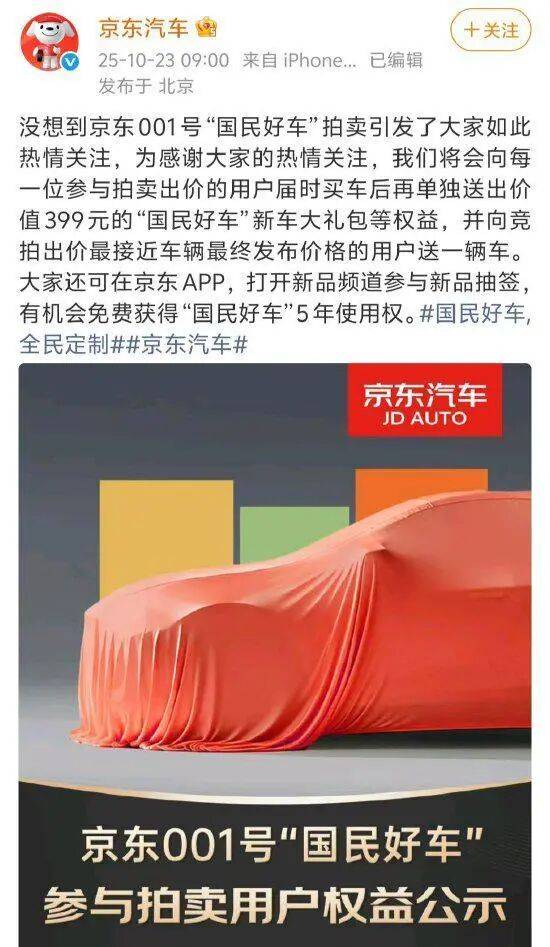
只不過,這份流量接下來要如何轉化,又將是擺在廣汽面前的一個最大問題。而對這場大戲的另一位主角京東而言,在2025年接近尾聲的時間節點用“造車”的噱頭賺足眼球,相信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也依然嚴峻。
在中國汽車產業深陷價格戰泥潭、產能嚴重過剩的當下,一家電商巨頭以“輕”姿態高調入局,究竟是順勢而為的明智之舉,還是在行業低谷期的一場讓人看不懂的賭注?
行業“至暗時刻”,為何成了京東的“入場券”?
當前,中國汽車產業的產能利用率已跌破50%的警戒線,創下近十年新低。與此同時,新能源滲透率高歌猛進,而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多數新能源品牌甚至到目前為止還未看到盈利的曙光。
全球咨詢公司艾睿鉑在7月發布的《2025全球汽車展望》年度報告中預測稱,目前市場上的129個新能源品牌中,能在2030年前實現健康盈利的或許不超過15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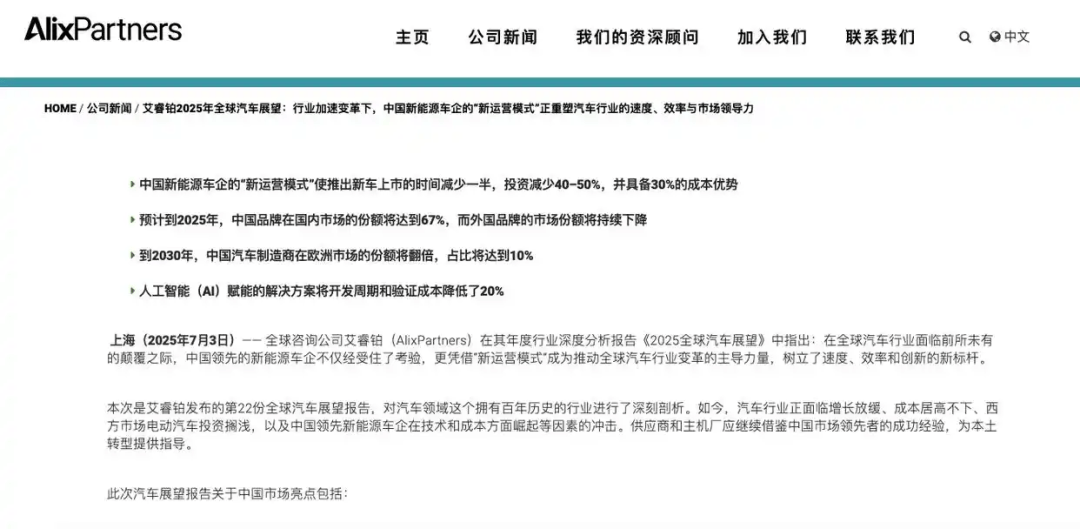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多數車企的日子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不好過”。
以此次與京東合作的廣汽埃安為例,其已經經歷連續數月乃至數年的銷量下滑,產品做到了“及格”甚至高性價比,但缺乏亮點,缺乏流量,就無法從這個追逐品牌效應和“爆款”的市場中脫穎而出,這也正是整個行業所面臨困境的縮影。
因此,當小米斥巨資自建工廠、華為深度賦能“界”字輩產品時,京東選擇的路線似乎指向了車企在發展中衍生出來的新“痛點”。
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兩個:一是傳統4S店模式難以為繼,銷售渠道變革的窗口期已經到來;二是隨著技術快速同質化,用戶關系的重構與服務體驗的價值才是“硬實力”的最終體現。

而京東就是帶著這一點,來尋找在此項上做得“不及格”的車企和品牌。
所以,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也正是汽車行業的深度內卷才意外地為京東這樣的平臺型企業創造了絕佳的入場機會。價格戰讓車企對低成本、高效率的銷售渠道需求空前強烈,而京東恰好能提供觸達數億活躍用戶的線上通道。
在生存壓力面前,車企與平臺合作的意愿和接受度都大大提高,也讓京東獲得了過去難以想象的議價能力。
從這一角度來看,京東此時的入局并不算“晚”,甚至可以說是時機剛好。除了廣汽之外,長安、小鵬等企業與其接連簽下合作大單,目標直指其渠道能力,尤其在海外板塊的布局和發展,也正印證了劉強東的這一判斷,的確有著充足的商業邏輯支撐。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的,汽車市場整體處于“至暗時刻”,聲量與用戶的競爭是擺在所有企業面前的問題,而只是輕度參與的京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這些“弱勢”車企補全競爭力?
輕資產的“陽謀”,能解汽車消費的“近憂”嗎?
縱觀近年互聯網企業“跨界”造車的案例,實際上站穩腳跟、成為了行業佼佼者的只有“全造車”的小米和“半造車”的華為。
前者的品牌效應被完全轉移到了汽車行業,甚至相比原本的3C制造業而言更上一層樓。后者則因不直接造車的種種障礙經歷了漫長的市場觀察期,直到技術優勢得以驗證,才算真正在行業內站穩了腳跟。

因此,在傳統汽車制造業利潤不斷被壓縮的今天,越是輕資產投入,其回報比例也越“不容樂觀”,京東也不例外。想要不造車卻分汽車市場一杯羹,“站著把錢賺了”,京東就必須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核心價值。
目前來看,這份核心價值大概率來源于京東多年積累的兩大核心資產。
其一,是超過5000萬PLUS會員的龐大消費數據,這使其能夠精準洞察用戶偏好,甚至在整車設計階段就前置性地定義產品,此次與廣汽、寧德時代合作的“國民好車”便是例證。
其二,是京東養車已構建起的近3000家自營門店與超4萬家合作門店的線下網絡,這為它承接從銷售、養護到未來換電等一系列落地服務提供了堅實基礎。
因此,從線上選車、購車,到線下保養、維修乃至換電,京東所做的就是試圖構建一個完整的服務閉環,將一次性的汽車交易,轉化為持續性的服務收入和用戶粘性,換言之,它在汽車行業想要“搶”的,還是外賣大戰時挖美團墻角的同款生意。

然而,這種輕資產模式也并非毫無風險。首先,品牌信任的遷移是一大難題。汽車作為高價耐用消費品,用戶信任建立在長期的技術積淀和安全記錄之上,京東作為電商平臺,如何將其在零售領域建立的信任平移至汽車領域,仍需時間檢驗。
其次,京東這一模式服務閉環的脆弱性也同樣不容忽視,正如華為與車企之間幾種不同模式的磨合都花費了不少時間精力,而且最終市場給出的反饋證明,“華為掌握獨家話語權”的合作形式才是最有市場的正解。
那么,京東這種高度依賴外部伙伴的模式,任何一環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整個商業規劃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面臨破產。

此外,對于當下正處于淘汰賽關鍵階段的汽車市場而言,京東所面臨的一項更深層的問題或許是“接盤”風險的挑戰。未來,如果汽車行業的內卷繼續加劇,京東的輕資產模式能否真正抵御系統性風險,或許還需要時間的進一步檢驗。
寫在最后:
隨著汽車制造業的壁壘被“內卷”逐漸淡化,服務業的機遇便隨之浮現。京東的入局,為內卷中的中國汽車產業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啟示:在一個制造能力普遍過剩的時代,生態整合與服務運營能力,或許正成為比制造本身更稀缺、也更具價值的核心競爭力。
對于車企而言,京東顯然不是“解藥”,而只是彌補自身在這一領域能力不足的可能答案。而對京東來說,這條不造車的“造車”路,是通往新的商業增長模式的“捷徑”,還是一灘渾水?時間會給出答案。

